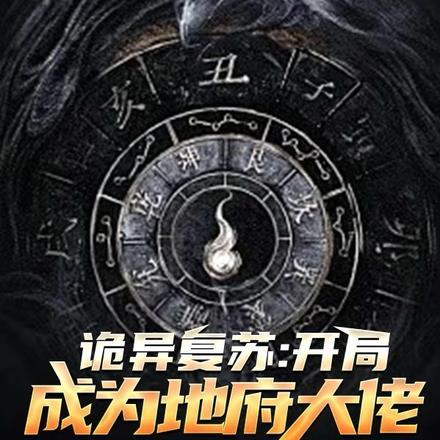爱看文学>妙厨 > 第六十一章 刀落(第3页)
第六十一章 刀落(第3页)
了一声,道:“你问吧。”
韩砺便请他坐了,又着人上茶,复才细致发问,先问架阁库归属哪一司,分管着哪些库,每一库构架编制多少人,再问现有多少人,岗位如何分配,职责如何。
那吏员不愧是在京都府衙多年,对上下情况了熟于心,一点也不慌忙,一一答了,其中有答得详细的,也有随意带过的。
韩砺便又把那几个被带过的问题拿出来再问。
他问得非常细致,譬如那某某司与某某司不是与某某年间合并了,又减了一员编制,为什么此时还有满员。
再问某某职责,原本不是应当归口某阁,什么现在又是分归某某处所管。
那吏员先还翘着二郎脚慢慢喝茶,一边喝,一边答,但眼见那韩正言一边问,一边还叫了个人在一旁用纸笔记录,心中忍不住打起鼓来。
“秦判官十分看重此事,为了有凭有据,人记毕竟不如笔记,还是写下来的为好。”
那韩正言解释完,又道:“不必担心,一会问完还会重新确认,确认之后,才会请你在上头签字。”
听得这一句,那吏员的心都要跳到了嗓子眼。
架阁库不是左右军巡处,只是管管档案、文书、账册,哪里见识过这样审讯一样的做法。
偏偏秦解秦判官又在里间坐着,他连个告辞的由头都不好找,也不能寻人帮着回去报告一声。
因不知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,那些问题又实在针对性十足,这胥吏答到后头,脚也不翘了,茶也不喝了,正襟危坐,老实听,慢慢答,不敢丝毫分心,唯恐说错了什么,要给对方逮住把柄。
他总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年轻人,而是一个同样下头做过许多年事的胥吏。
一问一答,足足花费了半个时辰。
眼见已经要收尾了,那胥吏听得对面那韩学生又问道:“你们楼务司平日里几人对外值守,几人守库?”
这一回,他回答起来就轻松多了。
楼务司原先只是管理官屋的,后来并入户曹,又分给了他们架阁库,眼下管着京城大小房屋产业文书档案。
但彼处只对外,并不对内,与左右军巡院几乎没有什么打交道的机会,自然也没有机会得罪,轮不到被当做小辫子来揪。
“平日里四人对外值守,两人守库。”
“若有百姓房屋买卖,前来报备,楼务司要几人确核?”
“一人确认,一人核对。”
“定契、房契、地契谁人出具?可有复核?可有签印?”
“俱有楼务司出具,一人出具,一人复核,俱有签名。”
“文书是否制式?”
“是为制式。”
“制式文书是为手抄,还是找坊子印制?”
“去找坊子印制,只有里头的房屋地址是我们后填进去的。”
“这文书是每年一印,还是用完再印?”
到了此处,这吏员却是笑了起来,道:“韩公子有所不知,府衙之中所有涉及银钱之事,都要招人‘买扑’,竞价之后,再做公示,一年一换,谁人都沾不得手。”
“这房屋产业文书也是如此,又因产业乃是民生大计,不得有半点马虎,故而印制时都有编号,领取之时也要登记,十分严格,旧的用完,才换新的。”
“那前一次换是什么时候?”
“这个月才换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