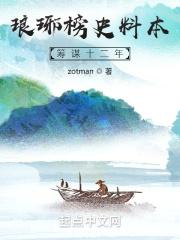爱看文学>醉金盏 > 第243章 做阿薇最趁手最随身的好刀完(第3页)
第243章 做阿薇最趁手最随身的好刀完(第3页)
后来的阿薇是内敛的,脾气不能外放,不张扬,这是她和闻嬷嬷的立身之本,她们是市井里极其普通的祖孙俩,如此才能隐姓埋名活下来。
再之后,她成了余如薇,且是虚假的、但陆念需要的余如薇。
她得有陆念一样的脾气,骄纵、张扬如盛夏,该动手时动手,该动嘴时动嘴,不露怯、不退让。
回京的这一年,算是把她隐姓埋名那些年“沉寂”
的力量,一下子全爆炸出来了。
以至于,当她重新成为金殊薇的时候,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无所适从。
“我也不是说这样不好,”
阿薇缓缓道,“就像我上一次和你说过,当我可以做选择时,当我有空闲、有余力来想七想八时,证明我已经往前又迈出了一步。”
沈临毓顺着她的思绪,问:“所以,是因为最近走得太快了些?”
阿薇思量了番,失笑道:“好像是。”
太快了,就像是才适应了一段风景,却闷头又穿过了一扇大门。
门后是全新的画卷,各处都美,让初来乍到的人一时目不暇接,不晓得该先往左、还是该去向右。
选择太多,竟也成了一种烦恼。
半合着的门被风吹开了些,沈临毓稍稍挪了挪杌子,挡住了风。
空中又飘雪了,洋洋洒洒的。
沈临毓整理着思绪,道:“你刚才的问题‘等大哥理顺朝政后,我会做什么’,我还没有回答你。”
“不是回避不答,是我近来也在反复思考,觉得走得太快了的,并不仅仅只有阿薇姑娘你,我也一样。”
“之前目标明确,翻巫蛊案、让大哥从舒华宫里出来,这些年朝堂行走,我做的事、无论大小,都是奔着这结果去的。”
“达成之后,我亦需要有一个新的、能一直指引着我的目标。”
“不敢说深思熟虑至成熟,但有大致轮廓。”
说到这里,沈临毓看向阿薇,四目相对,他认真又小心地问:“你愿意听一听吗?”
放在膝上的手指不由地收了下,阿薇端正地点了点头。
沈临毓开口时很有条理,显然是前后考虑良多。
“之前在广客来,说到蜀地那连打三回的案子时,我曾与阿薇姑娘你讲过。”
“朝廷需要明亮的眼睛,去看到那些力所不及之处的阴霾,否则就会养出一群欺上瞒下的土皇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