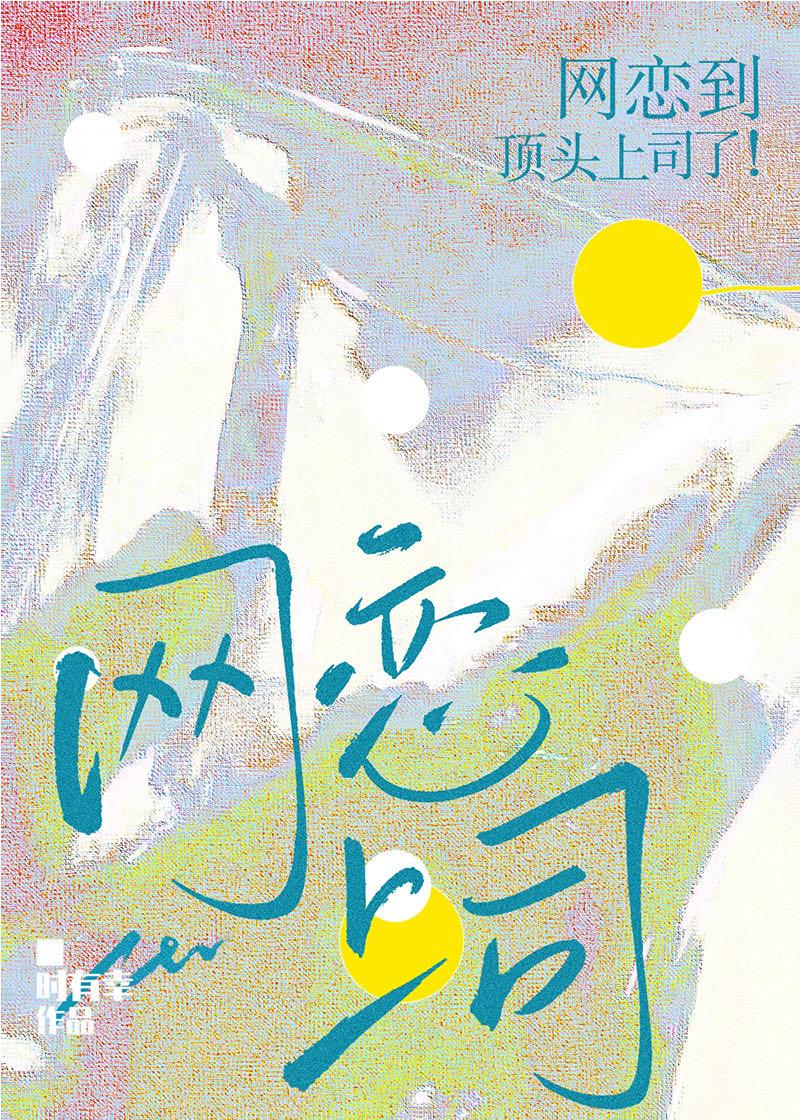爱看文学>四合院:傻柱开局瞎眼走新路 > 第306章 打幡摔盆(第3页)
第306章 打幡摔盆(第3页)
可我我实在没办法了啊"
一大爷张了张嘴,却说不出安慰的话。是啊,能有什么办法?八百块,对普通工人来说就是天文数字。
"
一大爷"
秦淮茹突然撑起身子,输液管被扯得哗啦作响。她手指死死攥住一大爷的衣角,声音压得极低,"
您您要是肯出这笔钱"
一大爷下意识要往后躲,却被她拽得更紧。晨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,照在秦淮茹惨白的脸上,那双哭肿的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。
"
我让棒梗给您打幡摔盆!"
秦淮茹几乎是咬着牙挤出这句话。
病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一大爷像是被雷劈中般僵在原地,连呼吸都停滞了几秒。打幡摔盆——这是儿子在父亲葬礼上才能做的仪式,是血脉传承最庄重的象征。
"
你你胡说什么"
一大爷的声音飘,手明显抖了一下。
秦淮茹却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越说越快:"
您无儿无女将来身后事总得有人操办棒梗虽然浑,但懂得报恩我让他给您披麻戴孝,当亲爹一样送您"
一大爷的喉结上下滚动。这话太诛心了。他今年六十二了,夜里常被同一个噩梦惊醒——自己躺在棺材里,连个摔瓦盆的人都没有。院里那些小年轻背地里都叫他"
绝户"
,他不是不知道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"
淮茹啊"
一大爷嗓子干,"
这不是钱的事"
"
八百块对您不算什么!"
秦淮茹急得又要咳血,"
您工资高,这么多年积蓄肯定够我求您了"
她突然从床上滚下来,竟是要跪下,"
我秦淮茹这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您!"
一大爷慌得去扶,输液架咣当倒地。隔壁床的老太太被惊醒,不满地嘟囔了几句。
"
起来!让人看见像什么话!"
一大爷使劲把秦淮茹往床上拽,看着她嘴角没擦干净的血痕,心里一酸。这才是什么样的母爱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