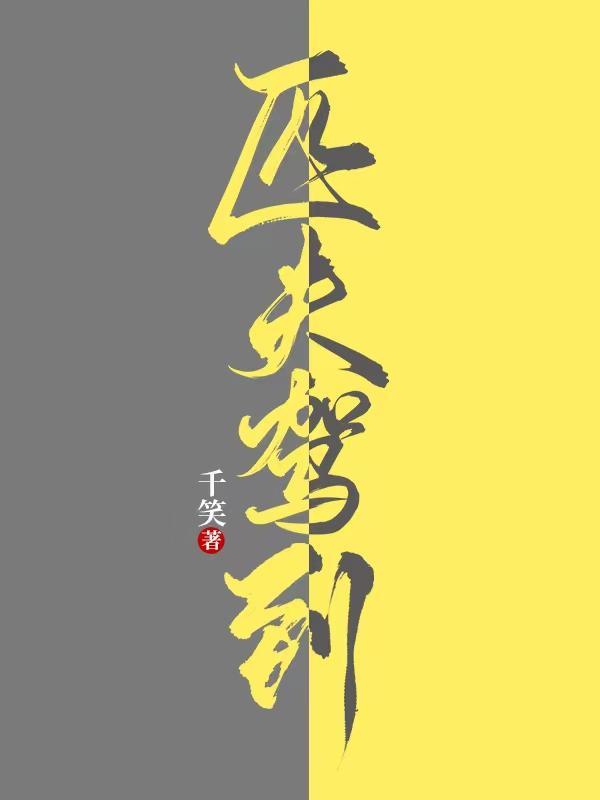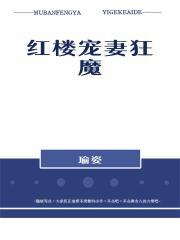爱看文学>自建帐以来:罗马汗国记 > 第115章 教堂要过火圣杯要过刀波西米亚人要换种(第2页)
第115章 教堂要过火圣杯要过刀波西米亚人要换种(第2页)
脱欢好奇道。
“这是习惯的代价,而不是宗教的代价。”
王大喇嘛如实说:“就我们见到的各种情况来说,改变教义比改变习俗简单多了。所以,一般来说,是宗教给习俗让路,而不是反过来。教会遇到的问题,也不是教义变化太少、太过死板;反而往往都是改的太多,灵活过头,导致异端频了。”
“而改变习惯,才是最难的。让一个地方的习俗变得更好,才是真正的教化。我们教会的‘教’,本来也应该是这个含义。”
他摇摇头:“可惜,无论是中原还是我们这边,能做到的人都太少了。谁要是能成功实现,那么无论在哪个文明里,都可以算个圣人,足以被后世一直铭记了。”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“一般来讲,民众日子过得越艰难,被欺压越严重的地方,教育水平就越低。百姓无从获取有用的知识,就只能依靠最简单的经验总结,躲避一切可能的危险,以求自保。这些习俗禁忌,就越牢固。”
郭康想了想,说:“所以波西米亚那边,算是情况还好了。埃及的平民,反而要麻烦一些。”
“我一直觉得,埃及这边的教育水平,要比欧洲整体都高不少呢。”
脱欢说。
“这倒是没错。但在整个地中海世界,教育水平这个概念,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人。没法和中原一样,简单地用学者们的文教水平,估计当地的教育风气。”
郭康摇摇头:
“在中原,有劝学的传统。尤其是科举制出现之后,民间的教育基础,和高级文人的数量,一直有一定关联。文教兴盛的地方,从事学习的人,基数就比较大,考出来的文化人也会比较多。但在这边,绝大部分百姓的受教育情况,和这个地区的教育水平,是没有关系的。想评估百姓的文化水平,可能还不如看基层的正规教堂数量,来的更准呢……”
“至于波西米亚那边,是出了意外情况。”
“他们那个国家,是卢森堡家族的主要根据地,所以,历代阿勒曼尼王,都会调动力量,进行建设。比如在欧洲,大学是给国王和贵族们提供顾问的重要组织,在教会里有很大的话语权。为此,之前的国王查理四世,就在布拉格建立了大学,来和巴黎分庭抗礼。”
“由于得到了整个阿勒曼尼地区的支持和投入,布拉格大学规模十分庞大。在查理末期的黄金时代,据说有十一万学生在这里就读。哪怕经过内乱,到o年的时候,依然有两百名博士和硕士,三百名学士,以及三万六千名大学生。”
“但是,布拉格大学,乃至波西米亚教会的高层,大部分都是阿勒曼尼人。学校里的权力划分,对本地人也很不利。巴黎大学那边,学校的自治机构,由法兰西、皮卡第、诺曼底、英格兰四个同族会组成,每个同族会有一票,因此,法国人总能在投票里占据优势。布拉格大学也模仿着设立了四个同族会,但它们是波西米亚、巴伐利亚、萨克森和波兰。其中,波兰学会里,也有大量是阿勒曼尼人。结果,人数最多的波西米亚本地人,反而没有对应的权力了。”
“后来,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迫于本地人的压力,提升了他们的投票权,宣布波西米亚同族会有三票,和阿勒曼尼人对等。但阿勒曼尼人又不能接受了。命令下达之后,当天就有两千名学生离校,以示抗议。几天后,陆续又有三千人选择离开。这些阿勒曼尼人回到了老家,自行组建了莱比锡大学,和布拉格分庭抗礼。”
“然而,学校的主要资助者,就是更加富裕的阿勒曼尼贵族和富商。教会和一些慈善团体,也会赞助贫困的教师和学生,但这些组织,也基本都是被阿勒曼尼人掌控的。阿勒曼尼学生集体出走之后,很多赞助也断掉了。师生的日子,也更加贫困了。”
“这种情况下,一些人选择借钱上学,结果欠了犹太人一屁股债。还有人则开始找地方打工。而就算是学校里的老师,待遇也十分微薄,只能到处找兼职做。因此,很多师生选择去其他地方当教师,来补贴学业。”
“最麻烦的是,哪怕学成之后,他们也没法获得好点的职位,因为整个伪神圣罗马内部,肥缺也都被阿勒曼尼人垄断了。就算波西米亚学者比较多,大家也只能去基层教会之类的地方抢个编制。到最后,连教会都装不下了。”
“结果,从最高级的布拉格大学以下,众多有知识的人,都只能去乡间,乃至上塔博尔山之类的地方去了。而这些意外情况,反而导致这段时间里,波西米亚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很多。胡斯派的众多变化,也是因为这些客观条件,才得以做到的。”
“我就说么。他们这么搞下去,都有点中原的意思了。”
脱欢了然地点点头:“这也是好事啊。”
“我之前还是低估他们了,没想到你评价这么高。我们可以考虑下之后怎么办了。假以时日,这地方应该会出现一个大国吧。”
“恐怕没这个机会。”
郭康摇摇头。
“为什么?”